按: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近日终于结案,依靠现代科技的进步,时隔33年通过DNA证据锁定嫌犯。这一连串发生于上世纪末的案件,成为无数影视作品素材,《杀人回忆》是其中的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一部。2003年,奉俊昊导演将这个连环奸杀案改编,创作出《杀人回忆》,电影一上映,立即在韩国国内引起轰动,超过500万人观看了影片。
“华城连环杀人案”发生于1986年至1991年间,有10名女子接连遭到绑架奸杀,其中仅有一人幸存。被害者年龄从十几岁至70多岁,跨幅度很大。此案当时造成韩国社会人心惶惶,民间广为流传着“不要在下雨天出门”、“女性不能穿红衣夜行”等说法。
最恐怖的是,犯下以上残忍罪行的犯人,平日是个很“温和”的人。现年50岁的李某,目前因1994年对自己妻子的妹妹进行强奸后杀害并且弃尸,被判无期徒刑,现收监在监狱中。根据狱友的回忆,李某服刑十几年间,从没有和人起过冲突,如果不是无期徒刑,现在很可能被评为模范犯人。甚至在服刑期间,李某发掘了自己的陶艺天赋,做出的陶艺作品屡次获奖。
如果不是留在现场那一点点细微的血迹,这个看似“无害”恶魔还会隐藏很久。今天这篇推文,来自哲学家对“恶”的思考。邪恶到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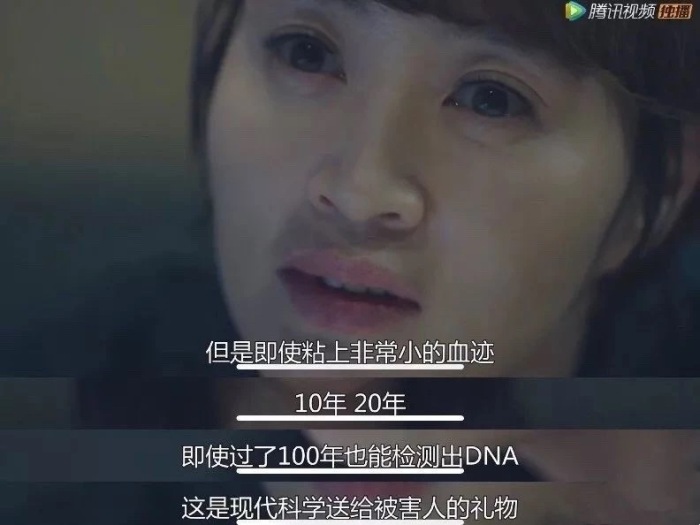
《哲学家与狼》
文 | [英]马克·罗兰兹 译 | 路雅

近来,邪恶的处境很艰难。这并非是说在我们身边,恶已经远去——事实完全相反——而是由于,许多所谓聪明人不愿承认其存在。
因为,在他们眼中,邪恶已是一个过时了的中世纪遗物——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自魔鬼撒旦,他恶毒的工作就是将邪恶注入男人与女人的内心去。因此,我们今日谈及“邪恶”,总是带着引号的。我们要么称它是一种物理上的问题——精神疾病造成的结果;要么将其看作社会问题——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风气带来的后果。相应便产生两种推论。首先,“邪恶”只存在于社会边缘,存在于心理或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人群中。
其次,它并非任何人的错。当一个人做了可能被我们称为“邪恶”的事情时,他们其实并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要么是有精神疾病,要么就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在医学或社会学意义上是不正常的,在道德上却并非是恶的。恶从不是它表面呈现出来的那样;邪恶总是另外的其他东西。我认为这些都是错的。那些现代的、所谓开明的关于恶的概念忽略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不是说我要为中世纪将恶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观点辩护。但是在现代恶的概念中,两点核心内容——恶只存在于社会边缘,以及,它不是某个人的错——在我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取而代之,我将向你们介绍一种关于恶的解释,听起来相当简单。首先,恶存在于非常坏的事物中。其次,邪恶的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因为他这一方存在过错。
让我们先试图理解,我们是如何变得如此怀疑“邪恶”这个概念的。现代对于邪恶的怀疑,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之上的:邪恶的行为需由邪恶的人来做;而邪恶之人的行动一定是出于邪恶的动机。如果因为疾病或者无法适应社会,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动机,那么你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在邪恶行为与邪恶动机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并非偶然。它要回溯到中世纪时关于“道德之恶”与“自然之恶”的区分上来。
中世纪哲学家,例如阿奎那,认为邪恶包括了痛苦、磨难以及相关现象,可以由两种不同的事物造成:自然事件与人为手段。地震、洪水、飓风、疾病、干旱等等,都可以造成严重而持续的痛苦。他们将因这种原因造成的痛苦与磨难称作“自然之恶”,用以区分由人为手段,也就是因人类做的恶而带来的痛苦与磨难。他们称后者为“道德之恶”。不过关于手段(或者行为)的概念也包括了动机或目的。一场地震或是洪水不带有动机;它并不行动,只是发生。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行动,可以做事情。但是,与某事发生在你身上不同,行动是需要动机的。掉下台阶并不是你做的事情,而是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有创造力的行为需要动机。因此,人们推断(尽管推断过程并不很严谨),一个邪恶的人是在邪恶动机的驱动下行动的。
这样一个结果是将道德之恶进行深度推理之后得出的。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身边最出色的哲学家之一,科林·麦金(Colin McGinn)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将道德之恶从本质上理解为一种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磨难以及不幸上(然而说实话,我认为科林无意将其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对道德之恶的解释)。这也许像是理解恶的一个好方法。但真的,恶就是为他人的苦痛与不幸感到高兴吗?而且,那些真的以此为乐的人可以代表所有邪恶之人吗?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种想法讲得通。

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孩提时代起就饱受虐待,从小就经常被亲生父亲强暴。你也许会像我一样惊恐地问:她父亲做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母亲在做什么呢?她难道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这个女孩的回答让我寒彻骨髓,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她说,每一次当她的父亲大醉而归,满嘴脏话,一心想打架的时候——这在她的家庭中是家常便饭——她妈妈会叫她到里面去,让他平静下来。每当我需要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确切的人性之恶的图景时,只需要想想这个妇人跟她女儿说的:到里面去,让他平静下来。
这里出现了两种邪恶的行为:父亲屡次的强暴、母亲主动的同谋。很难看出两者谁更恶劣。这位母亲也是一个受害者——这是当然——但难道她的邪恶就可以因此减轻吗?她拿自己女儿的身体、纯洁以及几乎是未来所有的幸福做筹码,交换自己从野兽一般的丈夫身边的片刻逃离。我们必须假定,她是出于恐惧才有如此举动,而并非在女儿的痛苦与折磨之中寻求快乐。但这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她的行为同人们所能想象的一样邪恶。每当你以为受害者不可能邪恶的时候,就想想这个例子。
如果说这对父母都不邪恶的话,那很难想象还有谁邪恶了。然而,无论是这位父亲还是母亲的行为,都不能通过动机的说法来合理解释,至少用麦金那种关于动机的想法来解释是行不通的。谁知道那父亲的动机何在呢?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也有可能不知道。假设他不知道,假设他认为这是家庭生活非常正常的一方面——也许他就是在类似的家庭环境之中长大的。也许他只是觉得事情就该是这样的。也许他认为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是他将自己的女儿带到世界上来,因此也对她有着完全的支配权——造物者对于自己所造之物的支配权。也许他觉得自己是在帮助自己的女儿——尽可能以一种调教的方式,来为她未来的性生活做准备。我只能说:谁在乎他是怎么想的。猜度他的动机在此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他认为自己什么也没有做错——甚至,即使他认为自做的是对的——也丝毫不能减轻他的恶。他的行为依然是可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恶行之一。
如同那位母亲一样,邪恶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尽到自己的保护责任而造成的,这与你在其中感到了多大的恐惧无关。邪恶也可能——像我们为那位父亲的动机所做的猜测性还原一样——是因为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蠢人。但无论是其中哪种情况,都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与不幸上”无关。我认为,故意造成的恶意同邪恶的本质无关。这并非是说,恶意在邪恶的行为中不起任何作用。我只是说,这样的事例还在少数。
现在让我们往后快进几年,哪怕只是想象一下,由于对女儿的折磨,这对父母被送上了法庭。我们假设这对父母最终被抓捕,受到惩罚——至于惩罚力度是否足够,尚有待争论。我不太确定,在这种情境下,女儿的心理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我想,也许会有些复杂。但假设没有,假设她是完全地为此高兴。进一步,假设她这种高兴并非出于认为漫长的监狱生活能够让他们重新做人——父母终于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帮助了。假设她高兴也并非因为不会再有别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了。再假设她高兴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审判对其他恋童癖者起到了震慑作用。假设她的高兴只是出于一个更简单、更基本的原因:复仇。

假设她希望自己的父亲受到的惩罚不只是绳之以法、失去自由那么简单。假设她更希望自己的父亲与一个喜欢鸡奸与强暴的大块头待在同一牢房,从而“自食其果”。那么我们要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吗?因为这样想,她就是一个邪恶的人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她对于复仇的渴望也许是令人惋惜的,因为这可能是其永久性心理创伤最终使其难以健全地生活的表现。也许。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孩难言邪恶。为极恶之人的不幸而感到欣喜,也许这并非道德发育与成熟的好范例,然而同邪恶还相去甚远。
因此,我认为幸灾乐祸对于成为邪恶之人来说,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它并非必要条件是因为,即使你不以他人的痛苦、折磨与不幸为快,你依然可以是一个恶人。就像那位母亲一样,你的恶也许是因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或者像我们为那位父亲做的动机推测性还原一样,你的恶也许是出于自己一开始的错误信念。同时,幸灾乐祸对于成为一个恶人来说也并非充分条件。为恶者的痛苦感到高兴并不能自动地使你变坏,尤其是在你曾受过他们蹂躏的情况下。
许多人也许会对我将所罗门、卡明与温的实验同这位受虐待的女孩的例子放在一起说感到惊异——好像这样对她所受的痛苦有些轻描淡写。不过这种反应没有任何逻辑根据。这两个例子是类似的,背后都潜藏着这样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某种我们不能想象的痛苦与折磨。这些坏事是犯罪者一方的过失所带来的结果。这种过失是有关责任的过失。不过这涉及两种不同的责任。
一方面,是没有尽到道德责任(moral duty)。这种责任是保护那些无助的人,使他们免受那些以此认定他们处于弱势因而可牺牲的人的伤害。如果这不是一种基本的道德义务,那么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是。那位母亲就是没有尽到这种责任,而且,就她的处境而言,她的过失毫无疑问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但这也只可能减轻她的罪责,而不能消除。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责任,被哲学家们称作知识责任(epistemic duty)。这种责任要求人们对自己的信念做适当的审慎考量:检查是否有适合的证据为它们提供合理性,并至少确定是否有与其抗衡的证据。我们现在对知识责任的关注少之又少,以至于大部分人根本不将其视作责任(当然,这本身就是知识责任出现过失的表现)。在我们对那位父亲的动机进行重建后(或许不太合理),会发现他的过失就属于这种。
在所罗门、卡明与温,以及他们的无数仿效者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失。我们看到的是这样荒谬无疑、不具备合理性的想法,例如,用电击来折磨狗可以揭示出人类抑郁的本质——包括其各种各样的根源、病因以及表征。在他们身上,我们亦看到了道德责任的堕落:保护无力抵抗的有情生命(sentient creature)免受我们大多数人(幸好)难以想象的痛苦的折磨。
我们人类之所以没能看到世上的诸多邪恶,是因为我们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动机所遮蔽,没能看到其中潜藏着的丑陋。这样的遮蔽是人类独有的缺陷。只要我们仔细地去审视恶,观察其各种不同的形式与伪装方式,总能追本溯源地看到我们在道德责任或者知识责任方面的过失。那些出于制造痛苦与折磨的特定目的,并且乐在其中的恶只是特例。这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越来越多邪恶的行为与邪恶的人相继出现,远比我们能够想象或者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
当我们把邪恶当作精神疾病或者社会缺陷的时候,会认为邪恶只是特例:它只存在于社会的边缘。但实际上,邪恶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依附于暴力的父亲、共谋的母亲,也同时依附于荣耀而幸福的哈佛心理学家,而在我们看来,后者的行为仅是出于最好的人道主义关怀。
我也曾有过邪恶的行为;很多很多。你也是。邪恶平淡无奇、司空见惯。邪恶是平庸的。在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的出色分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作为SS(纳粹党卫军)的军官,艾希曼负责帮忙纳粹政权系统有序地灭绝犹太人。阿伦特提出,这样的罪行并非源于他施加痛苦与羞辱的渴望。他并没有这种渴望。她认为,他罪恶的行为是因为没有能力与受害者产生同理心,以及不能对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进行合理的审视。我赞同阿伦特提出的“恶之平庸”的观点。但是它是由我们的“不情愿”(unwilling),而非“不能够”(inability)导致的。所罗门、卡明与温不是没有能力检视自己的信念,他们只是不愿意而已。对他们而言,绝非没有能力保护狗免受进一步的伤害。他们只是不愿这样做。
康德曾经很正确地说过,“应该”(ought)暗示着“能够”(can)。当说到“你应该去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暗示“你能够去做”什么。相反地,当说“你应该不去做”——也就是“你不应该去做”——什么的时候,也暗示了你有能力不去做。若我们从“不能够”的角度来理解这种邪恶的平庸,那么它便给我们提供了太便利的理由:这件事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再做不到其他了。无能为我们撇清了罪责。但我认为,我们很难如此轻易地为自己开脱。
一个人未尽职责(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知识上的)的过失,都是根于不情愿而非无能的过失,是这铸就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恶。然而,邪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不是它,两种过失都无法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受害者的无助。
本文摘选自《哲学家与狼》,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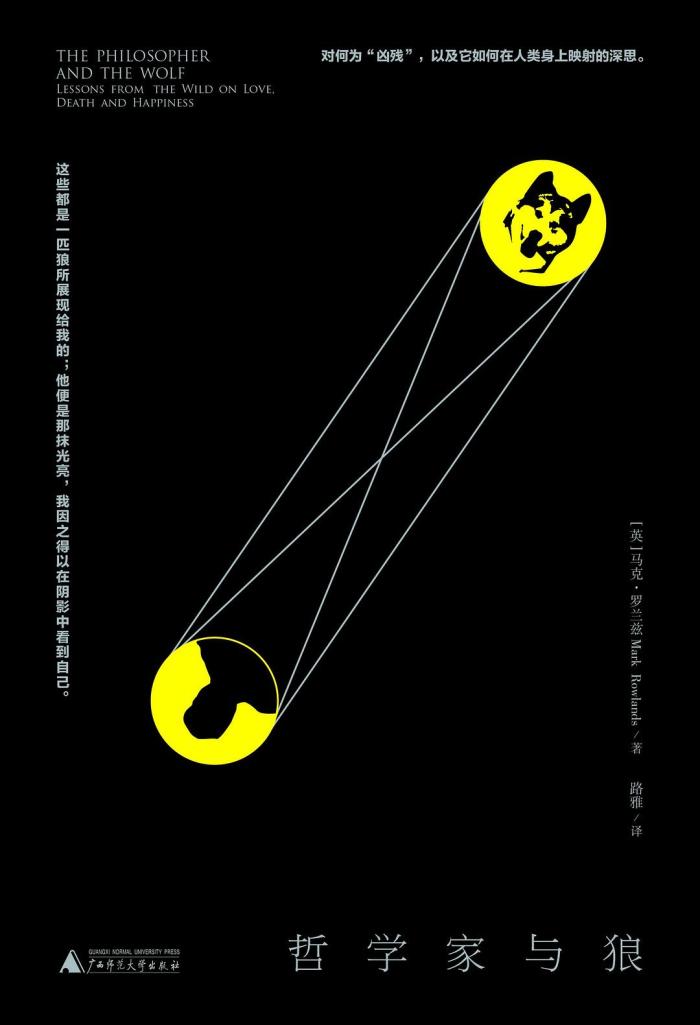
[英]马克·罗兰兹 著 路雅 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2
来源:新民说
原标题: 我们与恶的距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