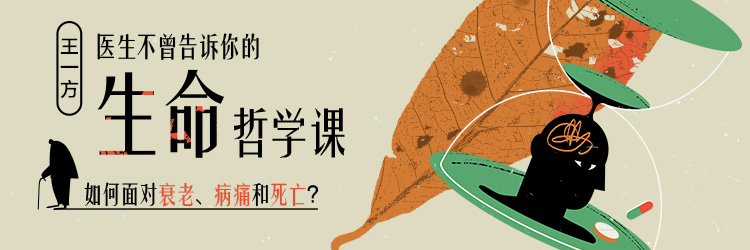中读
专访王一方: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应该如何做?
作者:吴淑斌
2023-06-27·阅读时长12分钟
专访王一方:中国人的死亡教育,应该如何做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似乎很少去讨论关于“死亡”的问题,也很怕提到“死亡”。为什么“死亡”让人这么恐惧?
王一方: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基因里面有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认知,因为在农耕文明中,一切追求存活率,一个动物或者植物的死亡就是一种失败。
我们经常讲怕死,“怕”字怎么写?左边一个“心”,右边一个“白”,就是心里一片空白。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带,所有人只会有一次“死的经验”,活着的人没有认知,一切都是迷茫的。
还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让人们害怕死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样的,但却清楚地知道,死亡后,现实世界里拥有的美食、美景、亲情、爱情、友情,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消失,这是一种对失去的恐惧;另外,死亡恐惧也来自于死亡过程中的痛苦,不管是中国古代的“酷刑”,还是现代人目睹癌症晚期病人、肿瘤病人的离世过程,都会觉得大部分死亡伴随着巨大的疼痛。所以很多人常说,理想的人生其实就是“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但似乎古代人有许多文学作品讨论生死,到了当下,人们反而更抵触死亡了?
王一方:在古代或近代,医学技术还没有这么发达,人们有一种共识:死亡是不可超越的。古代有战争、饥荒、瘟疫、动乱,这些天灾人祸对死亡的暗示非常强烈。近代医学还没有那么多ICU、抗生素、器官替代技术,危重病人十有八九会在短期内死掉,医生没有什么好办法,很多时候只能靠患者自己的力量扛着。人们当然也怕死,但心里都知道这是个正常、自然的过程,谁都无法对抗。
最近三四十年,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医疗技术发展得太快了,医院病床数、ICU数量大增,各种医学手段都在进步:心脏出问题了,可以做支架;血液不行可以换血;肾脏不行可以做透析;癌症和肿瘤也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化疗方案出现。社会上出现了“人定胜天”的心态,用技术极力阻止生命的正常凋零和衰亡。其实,人一直在经历局部的死亡,比如皮肤的脱落、细胞的更新,或者老了以后器官慢慢衰竭。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吊着,就被认为“没死”。这就是现代技术带来的期望,阻断重要器官的坏死,防止全面死亡——说白了,死是一个可以克服的事,“病”和“死”中间阶段无限延长,人就能“不死”。
患者和家属逐渐陷入一种思维误区:我花了许多钱,就是要“买命”的,而且一定能买到。医生也会有“英雄主义”情结,觉得有了先进技术的帮助,自己理应把人救回来。这样就会陷入“卒子过河”的困境:在生死面前,医生只能进,不能退;患者也不能接受亲人的离世,要用尽所有抢救手段,努力到最后一刻。
大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事实:医学是有极限的,它只能在某些时候拯救一个人。和死神的拉锯战中,最终获胜的都不会是人类。今天,我们单纯以“病人的复苏”作为对医生的评价标准是错误的:10个危重病人,救活了9个人的就是好医生,救活了7个的医生就不够好。把所有人都救活不符合自然规律,社会要建立一个新的标准:以患者在临终阶段的生活质量、生命尊严、生活品质为标准。一个医生没能抢救回濒死的病人,不是医生的失败;但如果病人去世之前,在你的手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安宁疗护,没有尊严和生活品质,去世的过程是冰冷、痛苦的,才是医生的失败。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其实应该让普通人和医生都建立一种对死亡的意识,学会如何去面对死亡?
王一方:是的。现在人们面对死亡时手足无措,就是因为在这一块上没有准备: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也没有行动上的安排。我们常说“预则安”,要对死亡有预案,才能安然面对。
我们现在的死亡教育非常不足。以前在农村,村子里都会有一个小广场,平时用来晒谷子,特殊时期拿来办红白喜事。这种村头的葬礼其实就是生活里的死亡教育,让活着的人经常看到,“人都是会死的,死了以后会有那么多哀伤的家属,这样处理后事”。大家陪亲属聊聊天,聚在一起悼念亡者,会听到这个人去世之前经历什么、家人和亡者还有哪些遗憾,心里多少会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现在,生活中能接触到死亡的场景越来越少,死亡流程也高度简约化了,在殡仪馆里鞠三躬、转一圈,就结束了,让人感觉“死”变得非常遥远。
对医生的死亡教育也不够。有一些医生很不愿意在最后的时间陪着病人,有的人是觉得自己“失败”了,很沮丧;有的人是觉得这段时间的抢救只是意义不大的体力活,比如重复的心脏按压。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拉着病人的手,凝望那双临终的眼睛,或者指导亲属如何与病人做最后的交谈、告别。医生的角色很重要,他们见过更多的死亡,是引导普通人面对自己死亡、亲人死亡的老师。问题是,现在很多医学生“灯下黑”,在医学院里,他们可能天天接触到“死亡”这个词,但对死亡的理解非常简单:心跳呼吸停止、瞳孔反射消失、心电图拉直。这是最浅显的生物学认知,死亡非常复杂,包含了对情感意志、社会关系的处理。
三联生活周刊:在医学院里,对医学生的死亡教育是如何做的?
王一方:我们会请很多人来开讲座,谈死亡的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概念,还有影视剧、电影里的死亡,这是前半部分,想让大家知道死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后半部分,我们会讲死亡过程中的安排,比如患者的生前预嘱、精神抚慰、音乐疗法,对家属的哀伤关怀等。
对于大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还是要把生活经验作为最主要素材。他们还没有进入临床,就把他当成一名普通的社会人来教导,只是传递一个理念:你将来会成为大夫,一定会面对许多人的离世,这很正常。未来的病房里,可能住着你的父亲、你的姨妈,有一天也可能住着你自己,但大多数是与你无关的普通人。你要把这份对亲人的情感平移到病人身上,不能因为是自己的亲人,就每天去关心关爱,对普通病人就简单地视为“37床”“48床”,自己只负责做单纯的技术干预。我们想要唤醒医学生的一种慈悲心,让他带着这一点知识的养料,到生活当中去体验情感。
对大学三年级以上、已经开始有临床经历的学生,就可以增加一些临床死亡教育了。开始让他们知道,如果病人到了癌症晚期,你可以告诉家属,病人的情况不太好,有可能最后会去世,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同时也让家属和病人开个家庭会议讨论,病人还有哪些心愿要完成。面对病人时该怎么去劝慰?你不能说“如果你死了,想让家属怎么做”,他接受不了;也不能说“你不要想太多,你会好起来的”,病人心里不糊涂。你可以考虑说:“你今天很疼,我完全理解,我们会想办法让你不那么疼。”见证苦难的过程很重要,一个人在那儿独自痛苦很难忍受,但如果有人来安慰和陪伴,就会好受很多。

三联生活周刊:但医学院里的学生都比较年轻,临床经验也少,“死亡”对他们而言还是个遥远的事情,死亡教育课的效果会好吗?
王一方:这个课的效果怎么样,不是上了一学期、两学期以后就能看出的,要进入临床之后才能得到反馈。还是学生时,他们接收到的是一种理念、暗示;进入临床后,才会慢慢锻炼成技能。我有一个北医毕业的学生去了吉林工作,后来我去开讲座,他又回来听我的课,跟我说:“我在北京听过了,但还是想再来。5年前您给我讲的东西,当时没有觉得很重要,现在才感到慢慢释放出来。”
生死观的转化不可能通过一个早上的课程就“齐步走”。上完课,也许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会对生死豁达一些,三分之一感到迷茫,三分之一甚至更加冷漠了——这完全有可能。在技术导向的环境里,有人会觉得“我已经给他做了各种技术干预了,我没有什么亏欠。至于是否投入了情感,是否做了心灵层面的抚慰,那不是我的任务。我害怕做,我不会做。”我们只能先影响一部分人,让他们对死亡有更深的理解。
还有很多人可能从未接受过死亡教育,而是在工作中受挫折后再回头思考这个问题的。这样的成本就比较大了。我到医院里给医生讲课,会感觉他们对学习“如何面对死亡”有强烈的需求导向。许多医生是带着自己的案例来的,一般都是自己受挫的经历,比如“对这个病人,该做的抢救我都做了,家属还是不理解我”,甚至还有挨打挨骂的情况。医生很委屈,但也有反思能力,会想如何才能改进,才来听讲座。我就告诉他们,除了抢救这些必不可少的事情,还可以做一些非技术性的抚慰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听起来,有时候其实就是需要医生多付出一些感情。
王一方:是的,医生的死亡观念、死亡教育,和人文关怀分不开。现在各种高精尖的技术有时反而造成了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隔膜。诊室里经常有这样的话:“你不要多说,赶紧去做检查,结果出来,一切都明白了。”影像技术的确很客观,可以马上把人脑袋里的沟沟壑壑重现出来。但很多人去看医生,是有倾诉的愿望、沟通的渴求的,病人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讲,有情绪要宣泄,有心理负担要解脱,这个过程也是治疗。
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发生在著名医学专家裘法祖先生所在的医院。有一次,裘老先生去查房,为一位老太太做了简单的腹部检查,因为老太太是胃疼住进来的,检查时,老太太哭了,裘老不理解,问她为何哭。老太太说:“我入院6天了,没人摸过我的肚子,您是第一个。”
要回归医学的本质,要把病人当作“人”来看待,而不是一个会喘气的瘤子,一堆各种各样的检查数据。我们提倡为病人写“平行病历”,除了一份记录病人检查指标和症状的病历外,还有一份记录病人的生活经历、家庭关系。医学是“人学”,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去病人的生活里寻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说一个人进了医院,如果还能治得好就是有价值的,治不好就没有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有医生跟你提到,工作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或是忘记了做那么多人文关怀的内容?
王一方:很多。真正有使命感的医生不会忘记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不只包括临终前对患者的安抚、写平行病历,哪怕只是给病人量体温时,用手摸摸他的额头这样一个简单动作,或者把听诊器搓热了,再倾身听病人的症状。但是常常有医生跟我说,自己很遗憾,本来想跟病人说某种话,或者安排某种东西,结果病人当天晚上突然就走了,还来不及找到一个窗口。你为什么要特地找一个窗口呢?有那么多事情,在平时的查房、门诊中,就已经可以完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医生、医学生,普通人的死亡教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王一方:我们当然会说,越早做越好,儿童时期就可以开始了。孩子5岁以前是没有死亡意识的,9岁开始会有自觉的死亡意识。对于儿童,可以通过读绘本讲故事的方法,给他们奠定一些理念,比如“人都是会死的,会到另一个世界去”。儿童对死亡其实没有那么恐惧,他们觉得这像躲猫猫,躲起来的人最终会重新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儿童死亡的照片就会发现,他们很安详,恰恰就是无知无畏。
对于成年人,其实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但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分社群进行。比如家里有残障儿童、癌症患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等,这些家庭最急需死亡教育。中残联给过一个数字,中国的残障人士目前是8500万,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4或者乘以6,就是家属的数量,非常庞大。这个人群的头上悬着一把剑,心里或多或少会感觉到,自己那位患病的亲人在可以预见的某一天一定会去世。对这样的群体,讲知识和理念的用处很小,可以让圈子里的典型人物去分享案例,讲讲患者和家属为死亡做了哪些准备,在去世后怎么走出哀伤。
除了这些重点人群,接下来就是经历过亲人、朋友离世的人。我们跟死亡之间是有“窗帘”的,爷爷奶奶是第一层“窗帘”,爸爸妈妈是第二层“窗帘”,每拉开一层“窗帘”,人就离死亡更进一步,面对死亡就显得更紧迫了一些。
面对死亡的准备,其实就是“道爱、道谢、道歉、道别”,要在家庭内部打开隔阂,更深入地相互了解。家属可以问问,病人还有什么想实现的心愿、想见的人,弥留之际想穿哪套衣服、听什么音乐,葬礼上希望由谁来致辞。听起来简单,许多人却做不到。很多时候,父母和孩子虽然有血缘关系、生活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
我见过一个老年患者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的遗嘱,包括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再接受积极抢救、死后有哪些安排,这本日记就放在家里的抽屉里,甚至都没有上锁,但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去找过。到最后,患者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儿子还是坚持要继续抢救——他不知道父亲早就安排好了。包括对待一些患病的老人时,很多子女总是说:“你不要想太多。”“你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这是多么浅薄的理解!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岁月和事情,怎么可能不想太多,这样的劝慰只会让他们更失落。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对成年人的死亡教育也是有紧迫性之分的。
王一方:当然。我们的精力有限,生活里有许多事情,只有紧急而重要的事情才会被重视起来。普通人接受死亡教育,更多的是一种自觉行为,不是一种集体行为,因为每个人的悲伤深度、对死亡的接纳和文化尺度是不一样的,要求全国一个方案来做死亡教育,不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普通人想自觉地接受死亡教育,有哪些渠道呢?
王一方:有大量关于死亡的电影、书籍可以选择,在一些地方还有“死亡咖啡馆”,大家在一个温暖的地方讨论关于死亡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听得多了,也就“脱敏”了。
按照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的说法,人一辈子当中有9次风险,其中3次是致命的,人和死亡就隔了一层纸。我常常会分享自己的一次经历,“我死过一次”。我年轻的时候是个船工,船在激流险滩上前进,螺旋桨经常打到岩石上就会坏掉,船失去动力,必须马上靠边把螺旋桨给换掉。下去换螺旋桨需要有很好的水性,尤其冬天水特别冷,还要观察有没有漩涡。有一次,我下船换螺旋桨时,就被漩涡吸下去了。当时漩涡的力量很强大,被卷进去的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钻出那个漩涡,干脆就放弃了,因为越挣扎人陷得越深。结果那个漩涡转了三五下之后,反而没有了向下牵引的力量,我那时候还有力气,拼命一滚,就滚出了漩涡。可能因为当时我没有拼命挣扎,也就没有感觉到被束缚得很痛苦,那一次体验了“濒死”的感觉。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么危险的经历,但可以听别人讲述他们的经历。在国外的一些地方还有“生命体验馆”,模拟人在濒死时的状态,在黑暗中看到一道光、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步入一个林中旷野。人体验过后就会觉得:“哦,死亡是这个样子呀!好像没那么可怕啊!”这就是“死亡脱敏”,对死亡不再是一片空白的迷茫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但即使有了准备,面对死亡时也还是会恐惧的吧?
王一方:肯定的。死亡就像要让一个人跳崖,去面对悬崖下面未知的一切。我们做死亡教育,就是给人提供一个降落伞,不是说有了降落伞,你就可以不跳下去,而是可以让你缓缓地着陆,心里不要那么惊恐,脑子里不是一片空白,甚至可以在降落的过程中注意看看两侧的风景。
(实习记者张雅文、方厚寅对本文有贡献)
▲点击图片进入中读音频专栏 《王一方·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
文章作者


吴淑斌
发表文章20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45人
真诚的交流。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全部评论(296)
发评论-

199*****538划线
05-15 18:20
我们做死亡教育,就是给人提供一个降落伞,不是说有了降落伞,你就可以不跳下去,而是可以让你缓缓地着陆,心里不要那么惊恐,脑子里不是一片空白,甚至可以在降落的过程中注意看看两侧的风景。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7:02
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岁月和事情,怎么可能不想太多,这样的劝慰只会让他们更失落。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8
“道爱、道谢、道歉、道别”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8
我们跟死亡之间是有“窗帘”的,爷爷奶奶是第一层“窗帘”,爸爸妈妈是第二层“窗帘”,每拉开一层“窗帘”,人就离死亡更进一步,面对死亡就显得更紧迫了一些。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7
对这样的群体,讲知识和理念的用处很小,可以让圈子里的典型人物去分享案例,讲讲患者和家属为死亡做了哪些准备,在去世后怎么走出哀伤。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5
你为什么要特地找一个窗口呢?有那么多事情,在平时的查房、门诊中,就已经可以完成了。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5
哪怕只是给病人量体温时,用手摸摸他的额头这样一个简单动作,或者把听诊器搓热了,再倾身听病人的症状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3
一个会喘气的瘤子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53
很多人去看医生,是有倾诉的愿望、沟通的渴求的,病人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讲,有情绪要宣泄,有心理负担要解脱,这个过程也是治疗。
- 0
- 0
- 0
-

199*****538划线
05-14 16:40
在技术导向的环境里,有人会觉得“我已经给他做了各种技术干预了,我没有什么亏欠。至于是否投入了情感,是否做了心灵层面的抚慰,那不是我的任务。我害怕做,我不会做。”
- 0
- 0
- 0
作者热门文章
-

致命的“忽视”:美国未成年枪手的父母获刑
0 40 33 -

失灵的“协议班”:中公教育“退费难”事件
0 100 87
推荐阅读
-

疾病的福利
13分钟阅读11 9 -

在中国和美国,我分别为家人善终
14分钟阅读67 55 -

医生的情感:如何对待你,我的病人
19分钟阅读106 93